布尔什维克是什么意思(什么是布尔什维克主义)
- 网站运营杂谈
- 2024-08-16
- 503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历史学家在研究1917年革命上做出了许多努力,许多研究想要去探究各个组织内外、处于底层的人们在想和做什么,而不是仅仅集中在尼古拉二世、亚历山大克...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历史学家在研究1917年革命上做出了许多努力,许多研究想要去探究各个组织内外、处于底层的人们在想和做什么,而不是仅仅集中在尼古拉二世、亚历山大克伦斯基或列宁的中央政治领导层。此前,如爱德华霍列特卡尔 (E.H.Carr)、伦纳德夏皮罗(Leonard Schapiro)、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和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这样的杰出研究者只将注意力集中在公共生活的最高点。新一代的历史学家开始关注工人、士兵、农民以及地方苏维埃和省级党组织。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之间的几个月对于那些试图阐明从下而上的历史的人来说非常有吸引力 S. A.史密斯(S. A. Smith)也是少数几个看到,如果不去仔细检视十月革命之后发生的事情,就无法解释中间这不寻常的8个月所发生的事情。

如今是时候仔细审视一番我们所发现的材料了,不仅仅是因为今年是俄国革命一百周年。史密斯这本书(《危机中的帝国:1890–1928年的俄罗斯》,Russia in Revolution: An empire in crisis, 1890–1928)的三分之一篇幅都在叙述1917年3月尼古拉二世退位之前发生的事情,他这么处理是有理由的。史密斯阅读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大量叙述。更重要的是,他对这些材料的呈现方式能够让对近期史学史不了解的读者更容易消化。他的目的是去强调结构性力量,而减少对诸如事故或个性等因素的叙述。他对于这段历史的阐述也不是没有考虑一些领导人作为个体的重要性,但相比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出版的大多数书籍,这些领导人在史密斯的书中所得到的关注要少得多。《危机中的帝国:1890–1928年的俄罗斯》强调一般的因素,这让人想起孟什维克领导人尤里马尔托夫(Yuly Martov)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世界》(Mirovoi bolshevizm,1923年),垂死中的马尔托夫在这本书里努力去从各个方面去解释许多事情,而不是什么事情都从自己最大的对手列宁身上找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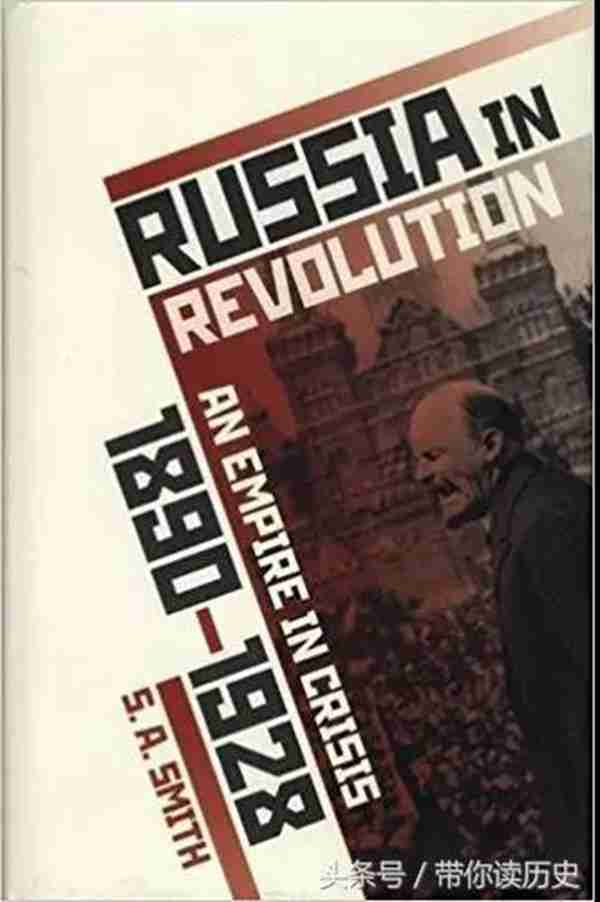
史密斯研究了沙皇时代末年经济进步与社会满意度之间存在的差距,并很好地回顾了贸易和工业的变化趋势。他驳斥了那种认为全体工人、农民在尼古拉二世统治下均生活困苦的过时观点。史密斯参考了新兵在被征召入伍时的身高等指标,他认为,入伍者身高的增长表明这些人的饮食水准比此前俄罗斯帝国的标准要高。他还介绍了近年来学界对当时俄罗斯农村的研究,强调农业中的商机令生活在新建铁路附近肥沃土地上的农民获益。西伯利亚西部出口黄油和乳酪,小俄罗斯和新俄罗斯(今日乌克兰在当年俄罗斯帝国地图上的称呼)出口小麦。莫斯科地区属于旧礼仪派(Old Believer)的纺织工厂老板对其员工的福祉抱有家长主义的关心。 然而,俄国大多数劳动者仍然生活得很艰辛,他们过的要比生活在柏林、米兰、伦敦或纽约的劳动者艰苦得多。一战前的几十年里,成千上万犹太人移民到美国或英国,对遭受迫害的恐惧并不是他们选择移民的唯一原因,他们也希望离开犹太小镇,寻求改善自己物质生活的机会。沙俄政府的财政部长谢尔盖维特(Sergei Witte)主导了19世纪90年代运输和制造业的扩张,他向外国商人保证俄罗斯的工人廉价、人数多且容易管教,成功地吸引了外商直接投资。 虽然人民在逐步获得更多教育机会以及成为工厂学徒的机会,但是他们的精神世界仍然被许多陈旧的观念所占据。那种对木精、恶魔和邪眼(译注:evil eye,由他人的妒忌或厌恶而生,可带来噩运或者伤病)的民间信仰很普遍。这些民间信仰持续对城市居民的心灵产生影响。当布尔加科夫在他亦真亦幻的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写到在莫斯科发生的奇怪事件时,他便借鉴了当时依然非常活跃的民间信仰传统。史密斯目前正在做一个有关俄罗斯和中国的魔术、宗教的比较研究项目,他将他的一些发现写进了书里,这部分也是整本书里最有价值的成果之一。这定然是一个值得重新考虑的主题。如果许多劳动者相信看不见摸不着的恶魔之力,在列宁、托洛茨基以及后来的斯大林声称全球资本家阴谋侵害工人阶级利益时,劳动者的这种信仰是不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他们这种说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关于布尔什维克政策与1917年投票支持布尔什维克的民众的愿望之间的边界的重要性,史密斯可能处理的不是很充分。1917年夏末到秋季这段时间,布什尔维克的支持率无疑有了很大的上涨,他们因而才能够接管工人和军人委员会(或者叫苏维埃),并组成武装部队,将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在彼得格勒的临时政府赶下台。列宁声称,这证明整个工人阶级认同共产主义的基本目标。这个说法过于夸大其词。东正教虽然在适应现代社会的种种境况上表现不佳,数百万俄国劳动人民对上帝的信仰依然没有变化。劳动人民为缓解自己的困境,拿自己的财产从小商贩手上换来他们需要的东西,他们也不知道为何这个共产主义国家为因此而惩罚他们。另外,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投票给地方上的布尔什维克,便是授权给布尔什维克建立起一个实施恐怖统治的国家。 《危机中的帝国:1890–1928年的俄罗斯》的优点之一便是将不同的、相互竞争的对历史的解读都展现在读者面前,由读者自己形成自己的想法。本着这种精神,史密斯本可以在他的总结中写得更尖锐些。自1914年起,列宁不只含糊地呼唤打内战,而且还提出了欧洲内战的口号。欧洲的军国主义本已令很多他的布尔什维克同志愤怒不已,列宁所表达的让更多人去送死的意愿让他们非常震惊。列宁1917年4月回到俄罗斯以后,他仍然在提这个口号,包括列夫加米涅夫(Lev Kamenev)在内的布尔什维克劝他缓和言论,以利于布尔什维克掌权。如果工人、农民被告知准备好被送上德国战场,没有多少人会把票投给布尔什维克。此外,迈克尔伯恩斯坦(Michael Bernstam)早在1982年就证实,十年革命发生后的几个星期内,反对苏维埃政府的工人起义就已经发生了,武装冲突非常激烈,直到新近建立的红军被部署来镇压这些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罢工者,工人起义才被平息下去。 然而, 史密斯非常重视这样一个事实:俄罗斯社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很久之前便受暴力所困。俄国内战中,双方迅速诉诸残暴手段对待敌方,强奸、酷刑和可怕的处决手段司空见惯。当时的宣传海报用极为鲜明的图像和语言描绘自己的敌人。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白俄就是一些贪婪、恶毒的资本家、主教和指挥官,他们肥肠满脑,腰缠万贯;对于白俄来说,布尔什维克就是一群反人类的犹太人,天真的俄国大众在他们的煽动下沉入无神论和野蛮的深渊。 马克斯坦伯格(Mark Steinberg)的书《俄国革命:1905-1921年俄国史》(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05–1921)所讨论的主题与史密斯的作品大致相同,但是斯坦伯格这本书的主观色彩更浓厚。斯坦伯格的语言有时让人读上去很费力,如斯坦伯格所宣称的,有血有肉的个体构成了他的书的核心。他的话似乎意味着,比起对事件进程的叙述,他对一些个体的生活经验更感兴趣。他的这本书的主要篇幅写的是1917年到1921年的历史。斯坦伯格过去写过一本颇有价值的作品(译注:指的是《无产阶级的想象:自我,现代性和神圣性》 Proletarian Imagination: Self, Modernity, and the Sacred in Russia, 1910–1925),以革命进程中一些卓越的个人的声音,特别是工人的声音为研究对象,他的新书便是建立在旧作的基础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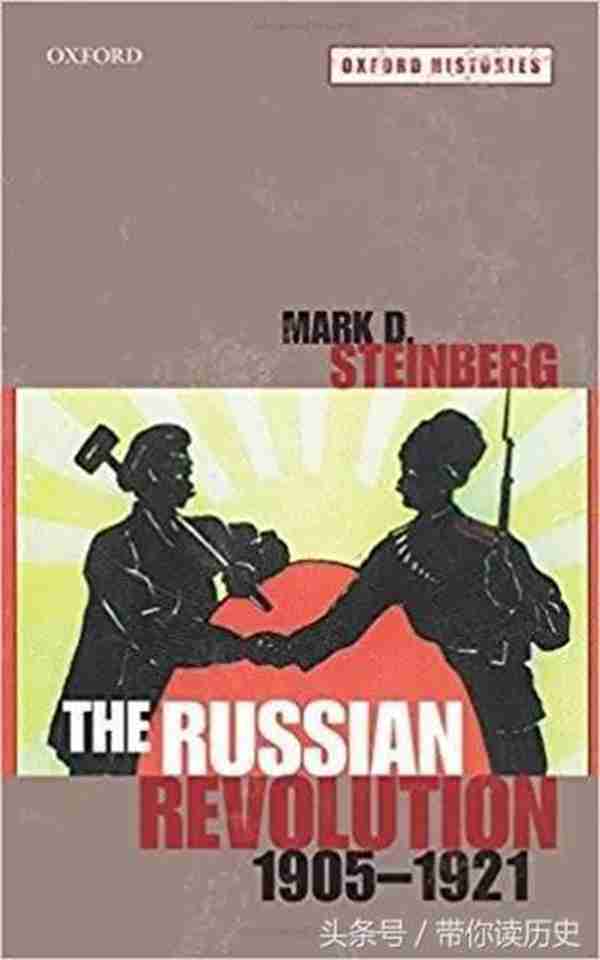
正是因为采用了这种研究方法,斯坦伯格才会既写流浪汉、穷困潦倒者,也写女权主义者亚历山德拉科隆泰(Alexandra Kollontai)、红军总司令托洛茨基和诗人马雅可夫斯基。通常情况下,他试图避免把他的解读强加在读者身上,而是倾向于让他书中的声音说话。很少有历史作品能够让这么多不同的民族 特别是乌克兰人、犹太人和中亚人民 的形象如此生动。斯坦伯格还研究了农民的独特经历,对他们的劳苦生活和反叛活动简短地描绘了一番。这样处理的目的一直以来都是为了将全体俄罗斯人民描述为地方革命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这是20世纪70年代历史学家的基本原则之一,这些历史学家挑战那种认为劳动人民一直被动地听命于革命知识分子的偏见。 斯坦伯格同情那些以一种理想主义精神发动十月革命的共产主义者。虽然他也描述了布尔什维克迅速转向专政和恐怖统治,他的语气总体来说是宽容的。斯坦伯格在对科隆泰、托洛茨基和马雅可夫斯基的处理上也很宽容,他将他(她)们称为乌托邦思想家,尽管三人生前都拒绝这个称呼。 对于斯坦伯格来说,他笔下的三位英雄之所以重要和有吸引力乃是因为他(他)们愿意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奋斗。他对科隆泰描摹了一番,也写到她试图创造一个让男女可以平等地生活在一起的新道德规范。科隆泰于1920到1921年间领导工人反对派(the Workers Opposition),她试图去维护布尔什维主义中平等主义一面。这些描述都是公平的,但是斯坦伯格忽视了工人反对派在与其他社会主义党派竞争过程中使用的不宽容手段。工人反对派成员首先是布尔什维克,其次才是平等主义者。斯坦伯格在写到托洛茨基时也很温和。和科隆泰一样,托洛茨基真诚地希望创造出一个人道的、文明的社会;另外,如斯坦伯格所说的那样,托洛茨基陶醉于 ‘街头所洋溢的生命力。但是,斯坦伯格认为托洛茨基并不是对高压政治和暴力最热烈的辩护者的观点则并不能为每个人所接受。斯坦伯格似乎认为列宁在这方面表现得更热烈。但是又是谁在1920年提出不让红军复员,而是改编为劳动军的呢?(译注:劳动军被组成之后,工人罢工就等于军人开小差,用托洛茨基的原话就是,应把开小差的工人关进惩罚营或送进集中营) 斯坦伯格在书中把马雅可夫斯基描述成了一个想要体验一种被彻底改造的生活方式的诗人。我们很难不同意这一点,而且马雅可夫斯基的《穿裤子的云》(Cloud in Trousers)足以证明他的文学天赋。但是,如果要说到对自己所经历的时代的理解能力,选择马雅可夫斯基来写就显得奇怪了。马雅可夫斯基1930年自杀,部分是因为他对共产主义革命之后发生的事情感到绝望,尤其是自己又成为了这场革命的桂冠诗人。但是,在马雅可夫斯基醒悟过来数年之前,亚历山大勃洛克肯定就对时代有了更多的感性理解吧?从十月革命开始,勃洛克就感受到了积极的民众参与所具有的复杂性。在他伟大的、粗糙肆意的诗歌《十二个》(The Twelve)中,街头的暗语被再现,感伤主义被拒斥,赤卫军、教士和妓女的形象在诗中都特别生动。勃洛克受这样一种观念影响:未来取决于不可预测的群众。他于1921年去世,但是如果他看到威权主义秩序在共产主义革命之后被建立起来,他应该不会像马雅可夫斯基那样震惊。 乔纳森斯梅尔(Jonathan Smele)的《俄国内战中的多场战争:震撼世界的十年》(The Russian Civil Wars, 1916-1926: Ten Years That Shook the World)是自伊万马德斯利(Edward Mawdsley)的权威作品《俄国内战》( The Russian Civil War)问世以来最雄心勃勃的对俄国内战这段历史的叙述。虽然史密斯梳理了关于民间政治和社会的最新文献,但斯梅尔似乎阅读了所有关于这个后来成为苏联的土地上发生的武装冲突的材料。斯梅尔勤勉、阅读量大,另外他还很勇敢。他特别对那种认为在那段时间中发生的战争主要是俄罗斯民族的内战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他还坚持认为,在这片原本属于俄罗斯帝国的土地上发生了多场内战。第三,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存在问题。如斯梅尔所说,远离东方阵线的第一次大型武装冲突发生在1917年二月革命前的中亚地区,尼古拉二世的政府征召当地的男青年作为劳工参战,而他们的伊玛目告诉他们,他们被组织起来的目的是为了打高加索阵线的穆斯林兄弟,后来成千上万名穆斯林起兵反抗沙皇政府。斯梅尔接着叙述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同时仔细审视爆发战争的边远地区。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的电影《十月》(October)在尊重史实上名声不佳,影片中表现的死伤人数比1917年秋攻占冬宫造成的实际死伤人数要多出许多。其他地方发生的强行接管所造成的死伤则要严重的多。例如,巴库发生的种族冲突造成数千名亚美尼亚居民被杀。十月革命发生后的几个月里,即使在俄罗斯中部和北部的工业城市,布尔什维克是否能继续掌权也并非确定无疑。用他们当时的说法,他们随时准备收拾东西走人。

如今是时候仔细审视一番我们所发现的材料了,不仅仅是因为今年是俄国革命一百周年。史密斯这本书(《危机中的帝国:1890–1928年的俄罗斯》,Russia in Revolution: An empire in crisis, 1890–1928)的三分之一篇幅都在叙述1917年3月尼古拉二世退位之前发生的事情,他这么处理是有理由的。史密斯阅读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大量叙述。更重要的是,他对这些材料的呈现方式能够让对近期史学史不了解的读者更容易消化。他的目的是去强调结构性力量,而减少对诸如事故或个性等因素的叙述。他对于这段历史的阐述也不是没有考虑一些领导人作为个体的重要性,但相比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出版的大多数书籍,这些领导人在史密斯的书中所得到的关注要少得多。《危机中的帝国:1890–1928年的俄罗斯》强调一般的因素,这让人想起孟什维克领导人尤里马尔托夫(Yuly Martov)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世界》(Mirovoi bolshevizm,1923年),垂死中的马尔托夫在这本书里努力去从各个方面去解释许多事情,而不是什么事情都从自己最大的对手列宁身上找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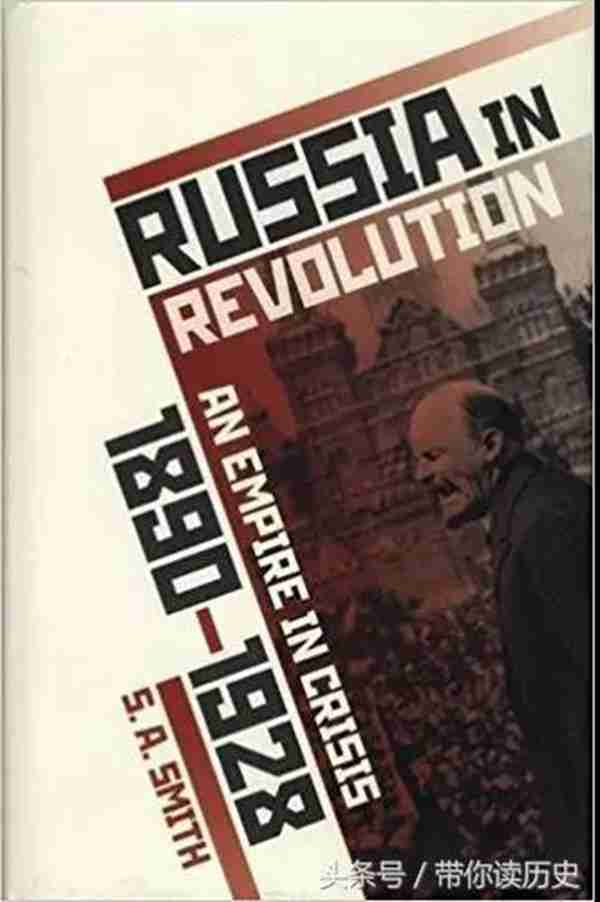
史密斯研究了沙皇时代末年经济进步与社会满意度之间存在的差距,并很好地回顾了贸易和工业的变化趋势。他驳斥了那种认为全体工人、农民在尼古拉二世统治下均生活困苦的过时观点。史密斯参考了新兵在被征召入伍时的身高等指标,他认为,入伍者身高的增长表明这些人的饮食水准比此前俄罗斯帝国的标准要高。他还介绍了近年来学界对当时俄罗斯农村的研究,强调农业中的商机令生活在新建铁路附近肥沃土地上的农民获益。西伯利亚西部出口黄油和乳酪,小俄罗斯和新俄罗斯(今日乌克兰在当年俄罗斯帝国地图上的称呼)出口小麦。莫斯科地区属于旧礼仪派(Old Believer)的纺织工厂老板对其员工的福祉抱有家长主义的关心。 然而,俄国大多数劳动者仍然生活得很艰辛,他们过的要比生活在柏林、米兰、伦敦或纽约的劳动者艰苦得多。一战前的几十年里,成千上万犹太人移民到美国或英国,对遭受迫害的恐惧并不是他们选择移民的唯一原因,他们也希望离开犹太小镇,寻求改善自己物质生活的机会。沙俄政府的财政部长谢尔盖维特(Sergei Witte)主导了19世纪90年代运输和制造业的扩张,他向外国商人保证俄罗斯的工人廉价、人数多且容易管教,成功地吸引了外商直接投资。 虽然人民在逐步获得更多教育机会以及成为工厂学徒的机会,但是他们的精神世界仍然被许多陈旧的观念所占据。那种对木精、恶魔和邪眼(译注:evil eye,由他人的妒忌或厌恶而生,可带来噩运或者伤病)的民间信仰很普遍。这些民间信仰持续对城市居民的心灵产生影响。当布尔加科夫在他亦真亦幻的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写到在莫斯科发生的奇怪事件时,他便借鉴了当时依然非常活跃的民间信仰传统。史密斯目前正在做一个有关俄罗斯和中国的魔术、宗教的比较研究项目,他将他的一些发现写进了书里,这部分也是整本书里最有价值的成果之一。这定然是一个值得重新考虑的主题。如果许多劳动者相信看不见摸不着的恶魔之力,在列宁、托洛茨基以及后来的斯大林声称全球资本家阴谋侵害工人阶级利益时,劳动者的这种信仰是不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他们这种说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关于布尔什维克政策与1917年投票支持布尔什维克的民众的愿望之间的边界的重要性,史密斯可能处理的不是很充分。1917年夏末到秋季这段时间,布什尔维克的支持率无疑有了很大的上涨,他们因而才能够接管工人和军人委员会(或者叫苏维埃),并组成武装部队,将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在彼得格勒的临时政府赶下台。列宁声称,这证明整个工人阶级认同共产主义的基本目标。这个说法过于夸大其词。东正教虽然在适应现代社会的种种境况上表现不佳,数百万俄国劳动人民对上帝的信仰依然没有变化。劳动人民为缓解自己的困境,拿自己的财产从小商贩手上换来他们需要的东西,他们也不知道为何这个共产主义国家为因此而惩罚他们。另外,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投票给地方上的布尔什维克,便是授权给布尔什维克建立起一个实施恐怖统治的国家。 《危机中的帝国:1890–1928年的俄罗斯》的优点之一便是将不同的、相互竞争的对历史的解读都展现在读者面前,由读者自己形成自己的想法。本着这种精神,史密斯本可以在他的总结中写得更尖锐些。自1914年起,列宁不只含糊地呼唤打内战,而且还提出了欧洲内战的口号。欧洲的军国主义本已令很多他的布尔什维克同志愤怒不已,列宁所表达的让更多人去送死的意愿让他们非常震惊。列宁1917年4月回到俄罗斯以后,他仍然在提这个口号,包括列夫加米涅夫(Lev Kamenev)在内的布尔什维克劝他缓和言论,以利于布尔什维克掌权。如果工人、农民被告知准备好被送上德国战场,没有多少人会把票投给布尔什维克。此外,迈克尔伯恩斯坦(Michael Bernstam)早在1982年就证实,十年革命发生后的几个星期内,反对苏维埃政府的工人起义就已经发生了,武装冲突非常激烈,直到新近建立的红军被部署来镇压这些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罢工者,工人起义才被平息下去。 然而, 史密斯非常重视这样一个事实:俄罗斯社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很久之前便受暴力所困。俄国内战中,双方迅速诉诸残暴手段对待敌方,强奸、酷刑和可怕的处决手段司空见惯。当时的宣传海报用极为鲜明的图像和语言描绘自己的敌人。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白俄就是一些贪婪、恶毒的资本家、主教和指挥官,他们肥肠满脑,腰缠万贯;对于白俄来说,布尔什维克就是一群反人类的犹太人,天真的俄国大众在他们的煽动下沉入无神论和野蛮的深渊。 马克斯坦伯格(Mark Steinberg)的书《俄国革命:1905-1921年俄国史》(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05–1921)所讨论的主题与史密斯的作品大致相同,但是斯坦伯格这本书的主观色彩更浓厚。斯坦伯格的语言有时让人读上去很费力,如斯坦伯格所宣称的,有血有肉的个体构成了他的书的核心。他的话似乎意味着,比起对事件进程的叙述,他对一些个体的生活经验更感兴趣。他的这本书的主要篇幅写的是1917年到1921年的历史。斯坦伯格过去写过一本颇有价值的作品(译注:指的是《无产阶级的想象:自我,现代性和神圣性》 Proletarian Imagination: Self, Modernity, and the Sacred in Russia, 1910–1925),以革命进程中一些卓越的个人的声音,特别是工人的声音为研究对象,他的新书便是建立在旧作的基础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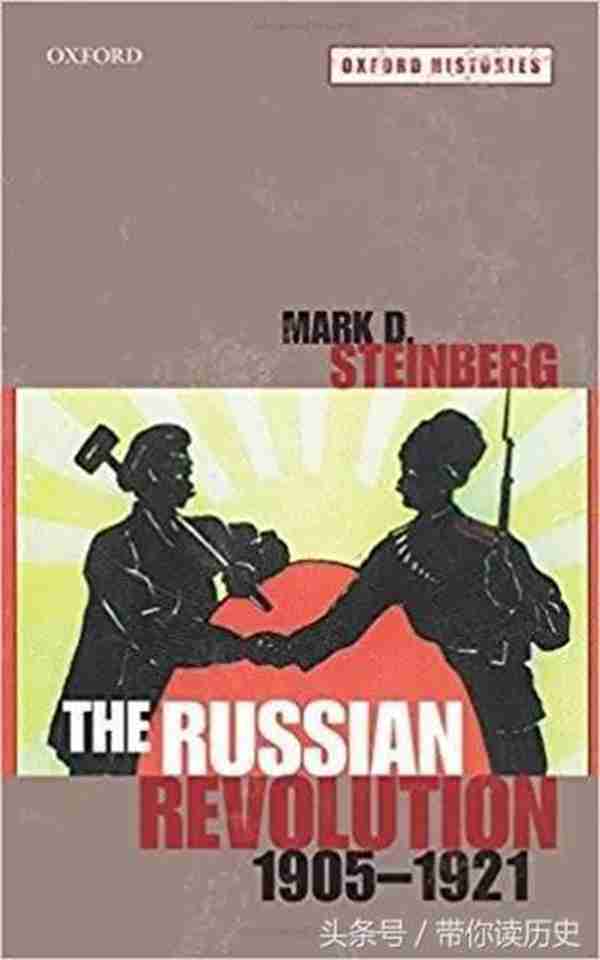
正是因为采用了这种研究方法,斯坦伯格才会既写流浪汉、穷困潦倒者,也写女权主义者亚历山德拉科隆泰(Alexandra Kollontai)、红军总司令托洛茨基和诗人马雅可夫斯基。通常情况下,他试图避免把他的解读强加在读者身上,而是倾向于让他书中的声音说话。很少有历史作品能够让这么多不同的民族 特别是乌克兰人、犹太人和中亚人民 的形象如此生动。斯坦伯格还研究了农民的独特经历,对他们的劳苦生活和反叛活动简短地描绘了一番。这样处理的目的一直以来都是为了将全体俄罗斯人民描述为地方革命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这是20世纪70年代历史学家的基本原则之一,这些历史学家挑战那种认为劳动人民一直被动地听命于革命知识分子的偏见。 斯坦伯格同情那些以一种理想主义精神发动十月革命的共产主义者。虽然他也描述了布尔什维克迅速转向专政和恐怖统治,他的语气总体来说是宽容的。斯坦伯格在对科隆泰、托洛茨基和马雅可夫斯基的处理上也很宽容,他将他(她)们称为乌托邦思想家,尽管三人生前都拒绝这个称呼。 对于斯坦伯格来说,他笔下的三位英雄之所以重要和有吸引力乃是因为他(他)们愿意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奋斗。他对科隆泰描摹了一番,也写到她试图创造一个让男女可以平等地生活在一起的新道德规范。科隆泰于1920到1921年间领导工人反对派(the Workers Opposition),她试图去维护布尔什维主义中平等主义一面。这些描述都是公平的,但是斯坦伯格忽视了工人反对派在与其他社会主义党派竞争过程中使用的不宽容手段。工人反对派成员首先是布尔什维克,其次才是平等主义者。斯坦伯格在写到托洛茨基时也很温和。和科隆泰一样,托洛茨基真诚地希望创造出一个人道的、文明的社会;另外,如斯坦伯格所说的那样,托洛茨基陶醉于 ‘街头所洋溢的生命力。但是,斯坦伯格认为托洛茨基并不是对高压政治和暴力最热烈的辩护者的观点则并不能为每个人所接受。斯坦伯格似乎认为列宁在这方面表现得更热烈。但是又是谁在1920年提出不让红军复员,而是改编为劳动军的呢?(译注:劳动军被组成之后,工人罢工就等于军人开小差,用托洛茨基的原话就是,应把开小差的工人关进惩罚营或送进集中营) 斯坦伯格在书中把马雅可夫斯基描述成了一个想要体验一种被彻底改造的生活方式的诗人。我们很难不同意这一点,而且马雅可夫斯基的《穿裤子的云》(Cloud in Trousers)足以证明他的文学天赋。但是,如果要说到对自己所经历的时代的理解能力,选择马雅可夫斯基来写就显得奇怪了。马雅可夫斯基1930年自杀,部分是因为他对共产主义革命之后发生的事情感到绝望,尤其是自己又成为了这场革命的桂冠诗人。但是,在马雅可夫斯基醒悟过来数年之前,亚历山大勃洛克肯定就对时代有了更多的感性理解吧?从十月革命开始,勃洛克就感受到了积极的民众参与所具有的复杂性。在他伟大的、粗糙肆意的诗歌《十二个》(The Twelve)中,街头的暗语被再现,感伤主义被拒斥,赤卫军、教士和妓女的形象在诗中都特别生动。勃洛克受这样一种观念影响:未来取决于不可预测的群众。他于1921年去世,但是如果他看到威权主义秩序在共产主义革命之后被建立起来,他应该不会像马雅可夫斯基那样震惊。 乔纳森斯梅尔(Jonathan Smele)的《俄国内战中的多场战争:震撼世界的十年》(The Russian Civil Wars, 1916-1926: Ten Years That Shook the World)是自伊万马德斯利(Edward Mawdsley)的权威作品《俄国内战》( The Russian Civil War)问世以来最雄心勃勃的对俄国内战这段历史的叙述。虽然史密斯梳理了关于民间政治和社会的最新文献,但斯梅尔似乎阅读了所有关于这个后来成为苏联的土地上发生的武装冲突的材料。斯梅尔勤勉、阅读量大,另外他还很勇敢。他特别对那种认为在那段时间中发生的战争主要是俄罗斯民族的内战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他还坚持认为,在这片原本属于俄罗斯帝国的土地上发生了多场内战。第三,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存在问题。如斯梅尔所说,远离东方阵线的第一次大型武装冲突发生在1917年二月革命前的中亚地区,尼古拉二世的政府征召当地的男青年作为劳工参战,而他们的伊玛目告诉他们,他们被组织起来的目的是为了打高加索阵线的穆斯林兄弟,后来成千上万名穆斯林起兵反抗沙皇政府。斯梅尔接着叙述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同时仔细审视爆发战争的边远地区。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的电影《十月》(October)在尊重史实上名声不佳,影片中表现的死伤人数比1917年秋攻占冬宫造成的实际死伤人数要多出许多。其他地方发生的强行接管所造成的死伤则要严重的多。例如,巴库发生的种族冲突造成数千名亚美尼亚居民被杀。十月革命发生后的几个月里,即使在俄罗斯中部和北部的工业城市,布尔什维克是否能继续掌权也并非确定无疑。用他们当时的说法,他们随时准备收拾东西走人。